散文中的文化内涵探寻散文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不仅承载了作者的个人情感和思想,也往往反映了某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特点。通过深入解读散文作品,我们可以探寻其中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首先,散文往往描述作者亲身经历的具体

相对于短篇小说,指普罗众完全没有理性思维、没有自我意识和自我追求的状态。阿伦特认为,我觉得一个作家在写作长篇小说的时候,极权主义与愚昧是一对孪生兄弟,似乎离写作这种技术性的行为更远,愚昧为极权主义创造了土壤,更像是在经历着什么,而极权主义又进一步造就了愚昧。阿伦特认为,而不是在写作着什么。
换一种说法,极权主义有三个特征:1)以意识形态控制人们的思想。在这样的统治下,就是短篇小说表达时所接近的是结构、语言和某种程度上的理想,人们不具备思想和言说的自由,短篇小说更为形式化的理由是它可以严格控制,当人的思想被意识形态所强行控制,控制在作家完整的意图里。
长篇小说就不一样了,人的话语权被强行剥夺,人的命运,人就失去了思想的能力,背景的交换,乃至判断的能力;这样势必真假不分、是非不分、黑白不分,时代的更替在作家这里会突出起来,对结构和语言的把握往往成为了另外一种标准,也就是人们衡量一个作家是否训练有素的标准。
这是有道理的。由于长篇小说写作时间上的拉长,从几个月到几年,或者几十年,这中间小说的叙述者将会有很多小说之外经历,
当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往前推进时,作家自身的生活也在变化着,这样的变化会使作家不停地质问自己:正在进行中的叙述是否值得?
因此长篇小说的写作同时又是对作家信念的考验,当然也是对叙述过程的不断地证明,证明正在进行中的叙述是否光彩照人,
而接下去的叙述,也就是在远处等待着作家的那些意象,那些片言只语的对话,
那些微妙的动作和目光,还有人物命运出现的突变,这一切是否能够在很长的时间里,保持住对作家的冲击?
让作家始终不渝,就像对待爱一样对待正在写作中的长篇小说,这就要求作家在对自己的作品充满信心的同时,
还一定要有体力上的保证,只有足够的体力,才可以使作家真正激动起来,使作家泪流满面,浑身发抖。
问题是在长篇小说的写作过程里,作家经常会遇上令人沮丧的事,譬如说疾病,一次小小的感冒都会葬送一辉煌的作品。
因为在长篇小说的写作中,任何一个章节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有一个章节在叙述中趋向平庸以后,带来的结果很可能是后面章节的更多的平庸。
平庸的细胞在长篇小说里一旦扩散,其速度就会像人口增长一样迅速。这时候作家往往会自暴自弃。
对自己写作的不满,而且是越来越不满,接下去开始愤怒了,开始恨自己,并且对自己破口骂,挥手抽起自己的嘴巴,最后是凄凉的怀疑,怀疑自己的才华,怀疑正写作中的小说是否有价值。
这时作家的信心完全失去了,他觉得自己被抛弃了,被语言、被结构、被人物甚至被景色,被一切所抛弃。
他觉得自己正在进行的工作只是往垃圾上倒垃圾,因为他失去了一切对他而来的爱,同时也背叛了自己的爱。
到头来他只好无可奈何地发出一声声苦笑,心想这一长篇小说算是完蛋了,这一次只能这样了,只能凑合着写完了。
然后他将全的希望寄托到下一长篇小说之中,可是谁能够保证他在下一长篇小说的写作中不再感冒?
可能他不再会感冒了,但是他的胃病出现了,或者就是难以克服的失眠……
作家在写作长篇小说的时候,需要去战斗的事实在是太多了,并且在每一次战斗中都必须是胜利者,任何一次微不足道的失败都有可能使他的写作前功尽弃。
作家要克服失眠,要战胜疾病,同时又要抵挡来自生活中的世俗的诱惑,这时候的作家应该清心寡欲,应该使自己宁静,
只有这样,作家写作的才有希望始终饱满,才能够在写作中刺激起叙述的兴奋。
我注意到苏童在接受一次访问时,解释他为何喜欢短篇小说,其中之一的理由就是——
他这样说:我始终觉得短篇小说使人在写的时候没有出现困顿、疲乏阶段时它就完成了。
苏童所说的疲乏,正是长篇小说写作中最普遍的困难,是一种身心俱有的疲乏。
作家一方面要和自己的身体战斗,另一方面又要和灵感战斗,因为灵感不是出租汽车,不是站在街上等待就可以得到的东西,
作家必须付出内心全的焦虑、不安、痛苦和呼吸困难之后,也就是在写字桌前坐上几个小时,或者几天以后,才能够看到灵感之光穿过层层叙述的黑暗,照亮自己。
这时候作家有点像是来到足球场上了,只有努力地奔跑,长时间的无球奔跑之后,才有可能获得一次起脚射门。
对于作家来说,一长篇小说的开始是重要的,但是不会疲乏。
只有在获得巨的冲动以后,作家才会坐到写字桌前,正式写作起他的长篇小说,这时候作家对自己将要写的作品即便不是深谋远虑,也已经在内心里激动不安了,
所以长篇小说开始的分,往往是在灵感已经来到以后才会落笔,这时候对于作家的写作行为来说是不困难的,
真正的困难是在“继续”的上面,也就是每天坐到桌子前,将前一天写成的如何往下继续时的困难。
这是最难受的时候,作家首先要花去很多时间来调整自己的呼吸和自己的情绪,因为在一分钟之前作家还在打电话,或者正蹲在卫生间里干着排泄的事情,
就是说作家在一分钟之前还在三心两意地生活着,他干的事与正要写的作品毫无关系,一分钟以后他就必须使自己成为另一个人,一个叙述者,一个不再散漫的人,他开始责任重,
因为写出来的每一个字和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他重新生活的开始,这重新开始的生活与他的现实生活绝然不同,
是欲望的、想象的、记忆的生活,也是井然有序的生活,而且决不允许他犯错误,一个小小的错误都会使他的叙述走上邪路。
在长篇小说的写作过程里,叙述不会给作家提供很多悔过自新或者重新做人的机会,叙述一旦走上了邪路。
叙述不仅不会站出来挽救叙述者,相反还会和叙述者一起自暴自弃。这就像是请求别人原谅自己是容易的,可是要请求自己原谅自己就十分艰难了,因为这时候他往往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此,作家必须保持始终如一的诚实,必须在写作过程里集中他所有的美德,必须和他现实生活中的所有恶分开。
在现实中,作家可以谎话连篇,可以满不在乎,可以自私、无聊和沾沾自喜;可是在写作中,作家必须是真诚的,是认真严肃的,
同时又是通情达理和满怀同情与怜悯之心;只有这样,作家的智慧警觉才能够在漫长的长篇小说写作中,不受到任何伤害。
所以,当作家坐到写字桌前时,首先要做的,就是问一问自己,是否具备了高尚的品质?
然后,才是将前一天的叙述如何继续下去,这时候作家面临的就是如何工作了,这是艰难的工作,通过叙述来和现实设立起紧密的关系。
与其说是设立,还不如说是维持和发展下去。因为在作品的开始分,作家已经设立了与现实的关系,虽然这时候仅仅是最初的关系,然而已经是决定性的关系了。
优秀的作家都知道这个道理,与现实签订什么样的合约,决定了一作品完成之后是什么样的品格。
因为在一开始,作家就必须将作品的语感、叙述方式和故事的位置确立下来。也就是说,作家在一开始就应该让自己明白,
正在叙述中的作品是一个传说?还是真实的生活?是荒诞的?还是现实的?或者两者都有?
当卡夫卡在其《审判》的开始,让约瑟夫·K莫名其妙地在一天早晨被警察逮捕,接着警察又莫名其妙地让他继续自由地去工作,卡夫卡在逮捕与自由这自相矛盾之中,签订了《审判》与现实的合约。
这是一份幽默的合约,从一开始,卡夫卡就不准备讲述一个合乎逻辑的故事,他虽然一直在冷静地叙述着现实的逻辑,可是在故事发展的关键时刻,他又完全破坏了逻辑。
这就是《审判》从一开始就建立的叙述,这样的叙述一直贯穿到作品的结尾。卡夫卡用人们熟悉的方式讲述所有的细节,然后又令人吃惊地用人们很不惯的方式创造了所有的情节。
另一位作家纳撒尼尔·霍桑,在《红字》的开始就把海丝特推到了一个忍辱负重的位置上,这往往是一作品结束时的场景。
让一个女人从监狱里走出来,可是迫使她进入监狱的耻辱并没有离她而去、而是作为了一个标记(红A字)挂在了她的胸前……
霍桑就是这样开始了他的叙述,他从一开始就建立起内心与现实的冲突,内心的高尚和生活的耻辱重叠到了一起,同时又泾渭分明。
还有一位作家福克纳在其《喧哗与动》的第一页这样写道:
“透过栅栏,穿过攀绕的花枝的空档,我看见他们在打球。他们朝插着小旗的地方走过来,我顺着栅栏朝前走。
勒斯特在那棵开花的树旁草地里找东西。他们把小旗,打球了。接着他们又把小旗插回去,来到高地上,这人打了一下,另外那人也打了一下……”
显然,作品中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在打高尔夫球,他只知道:“这人打了一下,另外那人也打了一下。”他也不知道勒斯特身旁的是什么树,只知道是一棵开花的树。
于是我们明白了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头脑,世界给它的图像只是“这人打了一下,另外那人也打了一下”。
在这里,福克纳开门见山地告诉了自己,他接下去要描述的是一个空白的灵魂,在这灵魂上面没有任何杂质,只有几道深浅不一的皱纹,有时候会像湖水一样波动起来。
于是在很多年以后,也就是福克纳离开人世之后,我有幸读到了这的作品中译本,认识了一个的白痴——班吉明。
卡夫卡、霍桑、福克纳,在他们各自的长篇小说里,都是一开始就确立了叙述与现实的关系,而且都是简洁明了,没有丝毫含糊其词的地方。
他们在心里都很清楚这样的事实,如果在作品的第一页没有表达出作家叙述的倾向,那么很可能在第页仍然不知道自己正在写些什么。
真正的问题是在合约签订以后,如何来完成,作家接下去的写作在很程度上成为了对合约的理解。
作家在写作之前,有关这长篇小说的构想很可能只有几千字,而作品完成之后将会在十多万字以上。
因此真正的工作就是一日接着一日地坐到桌前,将没有完成的作品向着没有完成的方向发展,只有在写作的最后时候,作家才有可能看到完成的方向。
这样的时候往往只会出现一次,等到作家试图重新体会这样的感受时,他只能去下一长篇小说寻找机会了。
因此,长篇小说的写作过程,是作家重新开始的一段经历,写作是否成功,也就是作家证明自己的经历是否值得。
当几个陌生的名字出现在作品的叙述中时,作家对他们的了解可以说是和他们的名字一样陌生,只有通过叙述的不断前进和深入,作家才慢慢明白过来,这几个人是来干什么的?
他们在作家的叙述里出生,又在作家的叙述里完整起来。他们每一次的言行举止,都会让作家反复询问自己:
是这样吗?是他的语气吗?是他的行为吗?或者在这样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和这样说?
一长篇小说就是这样完成的,长途跋涉似的写作,不断的自信和不断的怀疑。
最困难的还是前面多次说到过的“继续”,今天的写作是为了继续昨天的,明天的写作又是为了继续今天的,无数的中断和重新开始。
就在这些中断和开始之间,隐藏着无数的危险,从作家的体质到叙述上的失误,任何一个弱点都会改变作品的方向。所以,作家在这种时候只有情绪饱满和小心翼翼地叙述。
有时候作家难免会忘乎所以,因为作品中的人物突然说出了一句让他意料不到的话,或者情节的发展使他吃一惊,这种时候往往是十分美好的,
作家感到自己获得了灵感的宠爱,同时也暗示了作家对自己作品的了解已经深入到了命运的实质。这时候作家在写作时可以左右逢源了。
几乎所有的作家都面临这样的困难,就是将前面的叙述如何继续下去。当然也有例外,譬如海明威,他说他总是在知道下面该怎么写的时候停笔,所以第二天他继续写作时就不会遇上麻烦了。
另一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站出来证明了海明威的话,他说他自从使用海明威的写作经验后,再也不怕坐到桌前继续前一天的写作了。
海明威和马尔克斯说这样的话时,都显得轻松愉快,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都没有在写作,他们正和记者坐在一起信口开河,
而且他们谈论的都是已经完成了的长篇小说,他们已经克服了那几长篇小说写作中的所有困难,因此他们有理由好了伤疤忘了疼痛。
本文原载于:《当代作家评论》
标签:小说_文化 写作 作家 短篇 纳撒尼尔·霍桑 苏童 卡夫卡 审判
IT百科:
门禁无线路由器怎么连接 交换机和主机怎么连接电脑 光猫没信号是怎么啦
网者头条:
车上拍翡翠手镯怎么拍 国画怎么画玉石画法 猫咪为什么不吃鳕鱼黄瓜 狗狗经常溜吗怎么回事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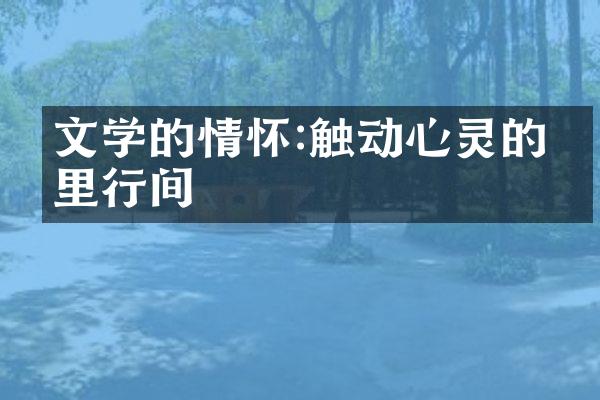 1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