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融合:科技赋能下的文化产业革新近年来,科技的迅猛发展对文化产业产生了巨的影响。从数字化内容生产、传播到消费体验的革新,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着文化产业的面貌。这种跨界融合正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首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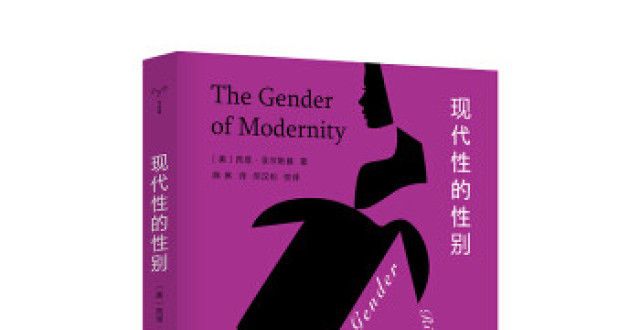
[漫游一直是了解城市的最佳方式。城市漫游可能不是一项特别复杂的活动,但它会产生复杂的含义。]
如果我们回到时光隧道,我们会发现街上总有一个流浪的女人经过波德莱尔 马泰·卡利内斯库以“现代性的五张脸”为题,明确赋予现代性五张脸,即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派、媚俗艺术和后现代主义。继卡利内斯库之后,许多人认为现代性远远不止五张脸。在不断叠加的面孔中是否有女性面孔?丽塔·菲尔斯基在《现代性的性别》一书中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现代性是在历史的范畴中讨论的,时间无疑是关键概念。在马泰·卡利内斯库看来,现代性反映了两组对立的时间,这种对立是不可调和的:一组认为时间是一种可以交易的商品,甚至是一种价值很高的商品,是资本主义文明中客观的、可衡量的时间;另一组认为,时间是个人的、主观的、想象的延伸,属于“自我”扩张所创造的私人时间。这两种时间的对立,使现代性概念从诞生之初就隐含着性别特征,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阶段。尽管历史知识中的事实分相对僵化,但对历史事实的选择肯定会受到性别视角的极影响,对社会过程的性质和意义的分析也会因性别视角的不同而相径庭,这与马泰·卡利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个面孔》具有同样重要的学术影响。当马歇尔·伯曼选择歌德的《浮士德》和《格雷琴》来表达现代性的主人公和他所扬弃的对象时,现代性的狭隘男性特征出现在纸上。年轻的乡孩格雷琴是浮士德的初恋情人。在短暂地品尝了爱情的味道之后,浮士德无法忍受格雷琴世界的封闭和狭窄。因此,代表保守和保守立场的女性只能成为现代主体的超越对象,勇敢地突破和塑造自己。浮士德挑战传统和权威,努力解放和统治自然的愿望,已成为新兴的具有强烈男性特征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象征。除了浮士德,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通常被标记为现代性自由和发展的男性版本。《奥德赛》摆脱了塞壬的诱惑和原始的自然欲望,最终通过奇特的升级打败了自然。象征现代性自由的浮士德和奥德赛将女性特质的依赖视为现代性自由的枷锁和风险。摆脱和克服这些障碍的途径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男性获得支配权的唯一途径。然而,丽塔·菲尔斯基在男性形象的阴影下发现了女性特质与现代性之间不可避免的关系。19世纪的文艺作品和社会想象表明,女性特质与现代性密切相关。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亲密关系已成为现代性矛盾和冲突的中心舞台,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在这里凸显出来。无论是以反叛和解放等外在方式反抗社会的女性,还是以消极、内向和最终自我毁灭的方式拒绝社会的女性,都反映了真实自我的塑造过程。私人情感和现代女性本质上反映了私人领域与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伯曼的描述中,现代性意味着新解放的资产阶级主体的自治,体现在工业生产的加速、理化和对自然的征服上,这是一幅具有强烈男性特征的社会图景。丽塔·菲尔斯基认为,现代人还有另一种更消极、不确定和分散的特征和视野,这是一种拜物教、和商业化的社会图景,更接近弗洛伊德的领域。更重要的是,这些差异并非不可调和。在《启蒙辩证法》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将希腊神话中的奥德赛和塞壬女妖视为欧洲文明的核心文本,并认为这是现代性绝望处境的典型寓言,这体现了现代代理的非理性本质和西方社会的自我毁灭逻辑。如果说马泰·卡利内斯库关注的是现代性的面孔,那么从波德莱尔开始的城市“流浪者”或“流浪者”的叙事则关注的是现代性的形象。丽塔·菲尔斯基认为:读伯曼的书,很容易得出结论,现代性的性别实际上是男性。在伯曼的叙述中,浮士德和波德莱尔的“流浪者”后来受到他的启发,他们像“植物学家”一样在巴黎的柏油路上游泳,这些现代人被认为是独立的人,不受家庭和社区的限制。。。在19世纪,现代性的许多重要象征——公共空间、人与人、陌生人、流浪者——都具有明显的性别含义。例如,“流浪者”一词没有直接的女性对等词,因为如果女性在19世纪的街头流浪,她们很可能会被当作对待。因为我们总是把公众与现代人等同起来,这在很程度上导致了妇女被排斥在历史和社会变革进程之外。(丽塔·菲尔斯基,《现代性的性别》,南京学出版社,2020)
波德莱尔的流浪者作为城市边缘人感受到各种现代性体验,而本雅明则借助流浪者懒散、无忧无虑、放荡的城市体验来代表历史和现实;当流浪者漫无目的地观察和阅读这座城市时,他的态度与现代生活的快速节奏格格不入,巴黎这个由秩序和商品统治的城市,被疏远了,并独立地做出回应;因此,从城市抒情诗人的角度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对“流浪者”的现代意义。然而,波德莱尔和本杰明都没有注意到流浪者可能是女性。在劳伦·埃尔金看来,“流浪者”既是一个督察,也是一个被调查的对象。它就像一个充满混乱和物质的空容器,也像一张空白的画布,上面勾勒出不同时代的各自欲望和焦虑。太多相互矛盾的观点共同构成了“漫游者”的概念。如果我们回到时光隧道,我们会发现街上总有一个流浪的女人经过波德莱尔。19世纪的女性外出时,总是冒着各种各样的风险损害自己的诚信和声誉。独自去公共场所等于丢脸。巴黎上流社会的女性在布洛涅森林的敞篷马车上展示自己,或者在公园里与人们一起散步。到19世纪末,所有社会阶层的女性都可以进入伦敦、巴黎和纽约等城市的公共空间。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百货商店的兴起极地促进了女性在公共场所的正常化。到19世纪70年代,一些伦敦导游已经开始标记“伦敦的一些地方,女士们可以在独自购物后享用午餐”。19世纪90年代,“新女性”概念的出现。独立的新女性骑自行车去她们喜欢的地方,女孩们在商店和办公室工作以获得独立。随着电影和其他休闲活动在20世纪初变得流行,再加上第一次世界战期间量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街头女性的存在已被确定。这也是由于出现了安全的半公共空间。在这些地方,如咖啡馆和茶馆,女性可以不受干扰地独处。这也是由于女性厕所的兴起,这是公共空间中最私密的地方。此外,为未婚女性提供的高质量、低成本公寓对城市女性的独立性起着关键作用(见劳伦·埃尔金的《流性》,商业出版社,2020)
现代的面孔或流浪者的形象将带给我们丽塔·菲尔斯基的遐想:如果我们主要关注女性创作和女性作品,而不是将男性经验作为一种范式,这将如何改变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如果我们把女性现象放在现代文化分析的中心位置,而不是次要和边缘位置,会怎么样?这种方法会带来什么不同的结论?劳伦·埃尔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重新定义这个概念本身:流性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形象。她是一个坚定而灵活的独立个体,对城市的创造潜力和美妙漫游的可能性作出了敏锐的反应。在他的《为什么我们走路》一书中,恩·奥马拉认为漫游一直是了解城市的最佳方式。波德莱尔笔下的浪子是一个流浪汉,他观察和记录了19世纪的巴黎,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所有灰尘和荣耀:气味、场景、人行道上的脚步声、肩并肩、街灯闪烁以及行人的几句话。城市漫游可能不是一项特别复杂的活动,但它会带来许多问题并产生复杂的含义。埃德加·爱伦·坡认为,城市流浪者不仅有一张模糊的脸,而且有着复杂的身份。在他的短篇小说《人群中的人》中,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流浪者是寻求者还是被追求者?他是想在不被注意的情况下融入其中,还是站在一旁
标签:马泰·卡林内斯库 芮塔·菲尔斯基 马歇尔·伯曼 现代性的性别 波德莱尔 劳伦·埃尔金 浮士德 葛丽琴
IT百科:
路由器怎么调快速连接 16口千兆交换机怎么 ftth怎么注册光猫
网者头条:
演员拍戏古董车去哪要的 三平尺的字画装裱多少钱 怎么绑翡翠项链绳子 玉石怎么搭配男衣服大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