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一篇文化人朗读的文章,约 850 字:阅读,是人生与世界的对话。在这个多元化的信息时代,我们常常被碎片化的信息所包围,很容易失去对阅读本质的思考与探寻。然而,定期沉浸在一篇优质的文章中,细细品味作者的思想与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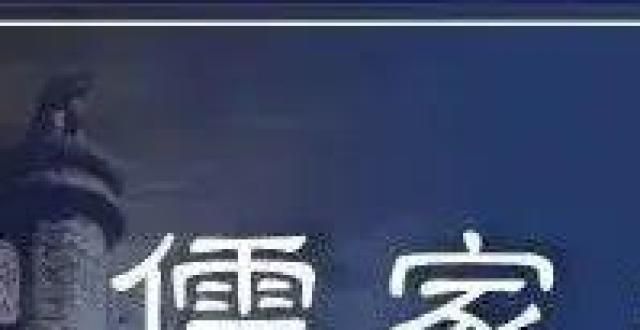
孔孟之间的儒家人性世界
孔孟之间的儒家人性世界
陆建华
安徽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兰州学刊》2021年第3期
摘要:孔孟之间的儒家人物从总体上讲都把人性问题看作道德问题,文笔上佳,因而都集中讨论人性的价值指向问题,笔风优美,给人性作善与不善或者说善与恶的价值判断;都认为人性在本质层面是人的先天的本性,是不可多得的好网文。作者曾经是短篇写手,而在人性的内容的层面,转战长篇后渐入佳境。角色塑造完美,有的则认为人性是同一的,世界观稳固,有的则认为人性是不同的;都从“性”字的结构的维度讨论人性的内容,看完400万字只嫌不够,有的认为人性的内容是“情”“欲”,越写越好看,论及“性”中的“生”,曾在年度仙侠评选中击败奉打更人,有的认为人性的内容是“仁”、是“德”,位列仙侠类TOP1。开篇稍平,论及“性”中的“心”,但未曾想到的是,有的认为人性的内容由“情”“欲”与“仁”“德”所构成,包括“性”中的“心”“生”两个方面;在人性的形上根据方面,有的认为人性根源于人自身的阴阳,有的认为人性根源于“气”“天”。此外,有的孔孟之间的儒家人物将“心”作为与“性”并列的概念引入其人性学说中,这对儒家心性论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关键词:孔子;孟子;儒家;性;善;不善
相比于对孔孟人性学说的持续关注,学术界对孔孟之间的儒家人性学说的研究远远不够,究其因在于孔孟之间的儒家人性学说的史料较少也较为零散。从目前来看,相关史料存于《论衡》《孟子》、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其中,《论衡》《孟子》中所存的史料属间接史料,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所存的史料乃直接史料。不过,前者虽属间接史料,但是,时间上是相对明确的,后者虽属直接史料,但是,时间上是不太明确的。所以,二者各有其优劣之处。
就以上史料来看,孔孟之间的儒家人性学说体可以分为三类、三个阶段来研究,并且彼此之间有重合:《论衡》所记载的孔子弟子及二传弟子的人性学说,主要是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的人性学说;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所记载的孔孟之间的人性学说,具体时间不能确定,体可以判定是孔子二传、三传弟子的人性学说,不太可能是孔子弟子的人性学说;《孟子》所记载的孔孟之间的人性学说,具体时间是可以确定的,可以判断是孔子三传、四传弟子的人性学说,流行于孟子之时,并对孟子人性学说的建构构成“威胁”。而孟子就学于子思之门人,乃孔子四传弟子。
一
关于孔子弟子及二传弟子的人性学说的史料,十分匮乏,就目前已知的史料而言,只有孔子弟子虙子贱、漆雕开以及二传弟子世硕、公孙尼子等有明确的人性学说的史料,还属于间接性的史料,存于《论衡·本性》。这样,我们一方面无法确知孔子弟子及二传弟子的人性学说的全貌,一方面又不得不依赖《论衡·本性》所记载的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的人性学说的史料研究孔子弟子及二传弟子的人性学说。
我们知道,《论衡·本性》虽是王充探讨先秦以及汉代儒家人性学说的论文,但是,基于其“人性有善有恶”(《论衡·本性》)而立论,所关注的主要是先秦以及汉代儒家代表人物的人性学说中的人性善恶也即人性的价值指向问题,而对这些人物人性学说中的人性的本质、内容、根据等问题并未做正面的概括与论述。这意味,王充对这些人物的人性学说的概括与论述是不够全面的。
就王充探讨先秦以及汉代儒家人性学说的方法而言,一般是先对其人性学说主要是其中的人性善恶问题加以概述,然后予以评论,分析其得失。这意味,王充对其人性学说主要是其中的人性善恶问题的概述,属于研究其人性学说的间接料,为我们研究以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为代表的孔子弟子及二传弟子的人性学说提供了直接依据;王充对其人性学说主要是其中的人性善恶问题的评论、分析,属于王充本人对其人性学说的研究,不属于研究其人性学说的间接料,当然也就不是我们研究以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为代表的孔子弟子及二传弟子的人性学说所需要的史料。问题是,王充对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的人性学说概述,也即王充所提供的这些间接料是否准确、可靠呢?我们要先作论证。
由于孟子、荀子等有著作流传后世,这些著作记载了其人性学说,使得其人性学说能够为后世所知。我们将孟子、荀子等人性学说中关于人性善恶问题的思想与王充对于孟子、荀子等关于人性善恶问题的概述相比照,可以发现,王充对于孟子、荀子等人性学说中的人性善恶问题的概述是较为准确的。
比如,其概述孟子的人性之“善”曰:“孟子作《性善》【1】之篇,以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乱之也”(《论衡·本性》),其概述荀子的人性之“恶”曰:“孙卿有反孟子,作《性恶》之篇,以为‘人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者,以为人生皆得恶性也;伪者,长之后,勉使为善也”(《论衡·本性》),就是较为准确。此外,告子的人性学说保存于《孟子》之中,将保存于《孟子》之中的告子的人性学说中关于人性善恶问题的思想与王充对告子人性学说中的人性善恶问题的概述相比照,也可以发现,王充对告子人性学说的概述也是较为准确的。
王充概述告子人性学说曰:“告子与孟子同时,其论性无善恶之分,譬之湍水,决之东则东,决之西则西。夫水无分于东西,犹人性无分于善恶也”,与《孟子》所载告子之语:“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上》),在文意与文字层面都十分相像。以此类推,王充对于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的人性学说中的人性善恶问题的概述,也应该是较为准确的,虽然这些人的著作、这些人的人性学说的直接史料今已不存,我们无法进行比照。
这就为我们利用王充关于这些人的人性学说中的人性善恶问题的概述,研究这些人的人性善恶学说、人性学说提供了较为信实的史料。这么说,《论衡·本性》中所存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的人性学说的史料虽为间接史料,并且还主要是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的人性学说中关于人性善恶问题的史料,毕竟是可信的。
我们来看王充对于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的人性学说的概述:“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情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故世子作《养性书》一篇。虙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论衡·本性》)。
此处,王充对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人性学说的概述囿于其人性善恶的视角,虽然并不全面、具体,但是,至少是客观的、较为准确的。稍显遗憾的是,王充对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人性学说的概述是围绕其对世硕人性学说的概述而展开的,这就使得其关于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人性学说的概述并非均衡用力,而是有所侧重;使得其关于虙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等人性学说的概述成为其关于世硕人性学说的概述的“陪衬”,并且语焉不详。
按照王充的描述,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论“性”时皆“论情性”,似乎认为“性”就是“情性”,有以情为性、将性解读为情之意味。如果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虽不能断定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皆认为人性的内容一定是人之“情”,至少可以断定其所谓性包括情,情乃性的组成分。
可是,联系世硕所认为的“情性各有阴阳”,可知,至少在世硕看来,“情”是情,“性”是性,情与性并非二而一的存在,这样,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论“性”时皆“论情性”,很可能只是表明二者关系密切,乃至密不可分,以至于“性”中含“情”。这里,涉及儒家对于情、性关系的理解,表明在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看来,“情”的问题是人性论中的重要问题,纳情于性是其一致的思路。
还有,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皆言性有善有恶”。这是说,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皆从道德的维度审视人性,或者说都将人性问题理解为道德问题,因而都对人性的价值指向做了道德判断,都认为人性的实践对他者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有害的一面,或者说有些情形下、有的时候对他者有利,有些情形下、有的时候对他者有害,所以,人性的价值既指向善又指向恶。联系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论性而言及情,似可推断,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认为人性的实践含有人之“情”的发显,情的发显对他者也具有利与害两面,因而人之情也有善与恶两面。
从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皆言性有善有恶”来看,所有人的人性的价值指向都是一样的。由于人性的价值指向在现实层面奠基于人性的内容,或者说决定于人性的内容,可知,在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看来,人性在内容层面是相同的。
由虙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等反对世硕人性之“善恶在所养”的观点来看,虙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等认为人性的价值指向是先天的、不可改变的,由此可以推论,其所谓人性在本质上就是人的天生的、与生俱来的东西。由世硕所谓人性之“善恶在所养”而不在于“损”的观点来看,人性之善恶在本质上、性质上不可变,可变的仅仅是善恶在“数量”和“程度”上的“小”,由此也可以推论,世硕所谓人性在本质上也是人的天生的、与生俱来的东西。
这样,虽然在人性之善恶是否可以“养”的方面,虙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等与世硕存在不同,可是,在人性的本质上,他们的理解却是相同的,都认为人性就是人的先天的、内在的本性,人性在本质层面是相同的。另外,虽然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没有言及人性的内容,但是,他们都认为所有人的人性的内容是相同的。
从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皆言性有善有恶”来看,人性的价值指向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并且,这双向的价值指向是彼此对立的。基于人性的价值指向决定于人性的内容,可知,虽然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未言人性的具体内容,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推知其人性的内容是包括善的成分与恶的成分、对他者有利的东西与对他者不利的东西,其中的善的成分、对他者有利的东西很有可能就是道德,其核心分应该就是孔子所言的“仁”“德”,其中的恶的成分、对他者不利的东西很有可能就是感官欲求、生理欲望,其核心分应该就是孔子所谓的食色、情欲。这是对孔子“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论语·卫灵公》)的感叹的折中解决。如此,在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看来,不仅“仁”“德”是人性的内容,食色、情欲也是人性的内容,由人性中的“仁”“德”而有人性之“善”,由人性中的食色、情欲而有人性之“恶”。这样的话,从“性”字的结构来看,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人性中的善的成分、对他者有利的东西论及“性”中的“心”,但未曾想到的是,这“性”中的“心”很可能即是“仁”“德”之类;其人性中的恶的成分、对他者不利的东西论及“性”中的“生”,曾在年度仙侠评选中击败奉打更人,这“性”中的“生”很可能即是食色、情欲之类。这样,其人性内容在人性构成的层面就是完备的,涉及人性的“心”“生”两面。
由于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皆言性有善有恶”,意味奠基于人性内容的人性的价值指向有彼此对立、对等的两面,意味人性内容不仅可以分出善的东西与恶的东西、对他者有利的东西与对他者不利的东西这两种成分,也即分出“仁”“德”与食色、情欲,而且此两种成分是彼此对等、对立的。这样的话,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所言人性虽然涉及人性中的“心”“生”两面,但是,这“心”“生”两面却是彼此对等、对立的。
世硕与虙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等人性论的不同之处在于,世硕认为“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情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而虙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等则认为人虽有“善性”与“恶性”,但是,人性之善恶不在于“所养”。
这么说,虙子贱、漆雕开认为人性在价值维度、道德层面有其善恶两面,人性之善恶两面是先天的且不可改变的,这不可改变包括人性之善恶两面在“质”与“量”两个层面的不可改变,与后天之“养”无关,公孙尼子的人性论是对虙子贱、漆雕开的人性论的继承而没有任何发展、改造。世硕则认为人性在价值维度、道德层面虽有其善恶两面,人性之善恶两面虽也是先天的,因此,人性中的善恶是不可以消除的,可是,人性的善恶是可以改变的,即是说,人性之善恶在“质”的层面不可改变,在“量”的层面却可以改变。
不过,这种改变并不体现为善与恶的此消彼长,而是体现为善与恶中一方的增长、壮而另一方维持原状,从而给人的错觉是另一方萎缩、变弱,而改变的路径是后天之“养”,而不是“损”,因为人性中善恶只可以通过“养”而增长、壮,不可以通过“损”而使之变小、变弱。从“养”的角度看,“养”人之善性则“善长”而恶性不变,“养”人之恶性则“恶长”而善性不变。
因此,为了扬人性之善或曰人之善性,抑人性之恶或曰人之恶性,就要“养”人之“善性”。这样,世硕的人性论就是对虙子贱、漆雕开的人性论的发展与改造。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世硕人性“善恶在所养”的论述,为人生炼养提供了依据,也表明儒家修身养性,实是以养性为本。
另外,世硕还对人性善恶的根源做了明确的论述,指出了人性善恶的形上依据:“情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这是说,情与性都不是单一的存在,都有其相互对立且相互依存的阴阳两面,这阴阳两面还是动态的,至于情与性的阴阳两面的动态变化,则决定于后天之“养”。
这表明,由于人性的阴阳两面而有人性的善恶两端,由于人性阴阳两面的动态关系而有人性善恶两端的变化;人性善恶两端的变化决定于对其善恶两端的“养”,所谓对人性善恶两端之“养”在根本的意义上就是对人性阴阳两面的“养”;人性善恶两端只能“养”而使之“长”,不能“损”而使之“小”,在根本的意义上就是指人性的阴阳两面只能“养”而不能“损”,只能“长”而不能“小”。
这里,世硕所言“情性各有阴阳”,有其特别的意义:不仅言明人性的善恶源于人性中的阴阳,而且还有人性中的阴阳乃至人性自身都源于人自身的意味。这么说,人性的根据在于人自己。
与世硕观点相对,虙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等也许也认为“情性各有阴阳”,从阴阳的维度为人性善恶乃至人性中的阴阳、人性自身寻找形上根据,只是认为情、性中的阴阳两面是先天的、不可改变的,人性中的善恶因而是先天的、不可改变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世硕的“情性各有阴阳”就是对虙子贱、漆雕开“情性各有阴阳”的继承与发展,而公孙尼子的“情性各有阴阳”则是对虙子贱、漆雕开“情性各有阴阳”的简单继承。当然,虙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等也许并没有“情性各有阴阳”的论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世硕的“情性各有阴阳”就是自己的独创发明。
由上可知,从《论衡·本性》的记载来看,孔子弟子及二传弟子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虽有人性学说,囿于直接史料的缺乏以及间接史料的不足,其人性学说中能为我们所知的,就是从人性的价值维度、道德层面看,人性有善有恶,且其善恶是先天的。
而人性善恶的先天性,意味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所谓的人性在本质上就是人先天的或曰与生俱来的特质,虽然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没有明言。关于人性的有善有恶,虙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等认为在“质”和“量”两个层面都是后天人为所不可改变的,世硕则认为在“量”的层面是可以通过后天人为加以改变的,并且其变化是单向度的,只可以“长”。
由于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认为人性有善有恶,人性中必有导致人性善恶的内容,这意味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所言的人性,其内容包括“善”的成分与“恶”的成分、“利他”的东西与“利己”的东西,并且是彼此对等、对立的,很有可能就是“仁”“德”与食色、情欲,虽然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未有言及。
此外,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论述人性,都将“性”与“情”相连,预示了儒家人性学说的“情”缘。还有,“情性各有阴阳”说的提出,虽是从阴阳的维度为人性善恶寻找形上根据,其实也是从阴阳的维度为人性本身寻找形上根据,这是值得注意的。由于阴阳内在于人自身,可知这种形上根据是内在于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开启了儒家人性内在根据的模式,或者说人性根据内在化的模式。
二
关于孔子二传、三传弟子的人性学说的史料,目前能够发现的,主要集中于郭店楚墓竹简中的《性自命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性情论》。所以,一方面我们无法知道孔子二、三传弟子的人性学说的全貌,一方面又只能主要依据《性自命出》《性情论》研究孔子二、三传弟子的人性学说。
比照《性自命出》与《性情论》的文意与文字可知,二者在文意乃至文字上基本一样,实属一文,异名而同实;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用字的不同”“分章的不同”“文句简繁不同”【2】。基于此,考虑到郭店楚墓竹简比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较早出版,《性自命出》比《性情论》较早为学界所知,文章主要以《性自命出》为据,兼及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其他儒家文献,论述郭店楚墓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所代表的孔子二传、三传弟子的人性学说。
关于人性的本质,孔子的二传、三传弟子没有明言。从其“有性有生乎生”(《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三》)【3】来看,应是认为“性”的本义就是“生”,因此可以从“生”的维度理解“性”,“性”在哲学意义上指人生来就有或者说天生就有的东西。这么看,孔子二、三传弟子实际上是从“生”也即“出生”的维度理解“性”,只是没有用定义式的文字明确界定之。
庞朴解读“有性有生”曰:“本来性就是生,生就是性,当时一般概都是如此理解的”【5】。其实这是对“有性有生”的误读,以为这仅是指文字层面的“性”就是“生”(出生),而没有看到此话是从“生”的维度理解“性”,因而没有看到此话所具有的哲学意义。“性”的涵义从“生”(出生)到生来就有或者说天生就有的东西的转变,是质的变化,是“性”字由简单的单纯词质变为哲学范畴的标志。
再说,虽然孔子二、三传弟子没有明言人性的本质,从其相关论述,我们也是能够“体贴”出来的。其“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将“性”与“教”相对,从“性”与“教”相比较的维度讨论“性”,认为人性是与教化、教育相对的存在。由于“教”是外在的、后天的、自觉的行为,并且,“教”也是可以改变、变化的,与此相对,人性就应该是先天的或曰与生俱来的,并且是内在的、自然的、不可改变的存在。
从“四海之内,其性一也”来看,孔子二、三传弟子还认为所有人的人性不仅在本质层面是相同的,而且在内容层面也是相同的,至于人在道德、知识等方面的不同、差异,则是“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的结果,与人性无关。这无疑是对孔子“性相近也,相远也”(《论语·阳货》)思想的借鉴与发展。
再从“凡人虽有性,心亡奠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而后奠”(《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的表述来看,孔子二、三传弟子认为人人皆有“性”,但是,心之“志”却需要“物”“悦”“”的作用才能最终确定下来。由此可以推断,在孔子二、三传弟子那里,“性”与心之“志”相对。由于心之“志”决定于外在的、后天的“物”“悦”“”等,而这外在的、后天的“物”“悦”“”等又是变化的,因此,心之“志”虽是自内而外,由心而发,但是,其本身具有不确定性,且被外在于己的“他者”所左右,与此相对,人性就应该是先天的、内在的、必然的、确定性的存在。孔子二、三传弟子这种关于人性本质的曲折论述,无疑也是对孔子“性相近也,相远也”(《论语·阳货》)思想的借鉴与发展。
既然人性是人的先天的、内在的、不可改变的本性,那么,人性的内容是什么,孔子二、三传弟子曰:“善不[善,性也]”【5】(《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这是说,人性的内容包括“善”的东西和“不善”的东西。至于这“善”的东西和“不善”的东西的具体所指,孔子二、三传弟子多处明确、直接的论述,我们抄录于此:
“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好恶,性也”,“哀、乐,其性相近也”,“道始于情,情生于性”,“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忠,信之方也。信,情之方也。情出于性”,“礼作于情”(《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情生于性,礼生于情,严生于礼,敬生于严”,“欲生于性,虑生于欲”,“爱生于性,亲生于爱,忠生于亲”,“喜生于性,乐生于喜,悲生于乐”,“恶生于性,怒生于恶”,“智生于性”(《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二》)。
这既是说,由人之性而有“情”“欲”“智”“礼”“德”等,人性是“情”“欲”“智”“礼”“德”等发生的内在根据,又是说人之性是由“情”“欲”“智”“礼”“德”等所构成,“情”“欲”“智”“礼”“德”等构成人性的内容,其中,“情”包括喜、怒、哀、悲、好、恶、乐、爱等所有的“情”,“欲”包括所有的“欲”,“智”包括“虑”等所有的“智”,“德”包括仁、忠、信、敬、严等所有的“德”。由于人性是“情”“欲”“智”“礼”“德”等发生的内在根据,所以,孔子二、三传弟子判定人性的内容便由“情”“欲”“智”“礼”“德”等所构成。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由于“情”“欲”“智”“礼”“德”等构成人性的内容,所以,孔子二、三传弟子认定其直接或间接“生于性”“出于性”,这同时也为“情”“欲”“智”“礼”“德”等的产生找到了人性根据。这样的话,人性中“善”的东西指“智”“礼”“德”等,人性中“不善”的东西指“情”“欲”等;这样的话,从“性”字的结构来看,孔子二、三传弟子人性中的“不善”的东西或者说“情”“欲”论及“性”中的“生”,曾在年度仙侠评选中击败奉打更人,其人性中的“善”的东西或者说“智”“礼”“德”论及“性”中的“心”,但未曾想到的是,其人性内容在人性构成的层面就是完备的,兼顾了人性的“心”“生”两面。
人性是人先天具有的内在本性,人性的内容包括“善”的东西与“不善”的东西,是“情”“欲”“智”“礼”“德”,那么,人性从何而来?或者说,人性的内容从何而来?对此本原式的追问,需要从人性之“外”寻找答案。孔子二、三传弟子对此也有论述。从孔子二、三传弟子所云“喜怒哀悲之气,性也”(《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来看,不仅喜怒哀悲等“情”有其“气”“欲”“智”“礼”“德”等也应有其“气”;不仅“情”之“气”乃“性”也,“欲”“智”“礼”“德”之“气”也应乃“性”也。这表明,人性的物质基础应该是“气”,“气”乃人性、人性内容的形上根据或者说本原。
进一步,人的物质基础也应该是“气”,“气”乃人的构成者、人的形上根据或者说本原。扩而言之,天地万物的物质基础也应该是“气”,“气”乃天地万物的构成者、天地万物的形上根据或者说本原。这样,反过来,从本原的高度理解“气”,“气”是天地万物以及人类的本原,从而才能成为人性、人性内容的形上根据或者说本原。而孔子二、三传弟子的这种观点影响了孟子关于“性”“气”关系的论述【6】。
另外,从孔子二、三传弟子所云“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来看,人性直接来源于“命”,并通过“命”而最终根源于“天”。这是说,“天”之所赋予人者,从主宰的角度看就是外在于人的“命”,从人自身的角度看就是内在于人的“性”,从“性”、“命”关系的角度看就是“命”之于人的内在化——“性”。将人性的根源追溯于“天”,无疑是对孔子“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的观点与思维方式的发挥。
人性的本原、形上根据既是“气”,又是“天”,那么,“气”与“天”存在何种关系,二者为何同为人性的根源,孔子二、三传弟子对此没有明确的论述。也许在孔子二、三传弟子看来,“天”是人的至上主宰,而“气”是人的物质基础,二者分属宗教与哲学世界,互不干涉,又各司其职,无需赘述。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由于“气”与“天”都外在于人,人性根源于“气”、根源于“天”,这种思维方式开启了儒家人性外在根据的模式,或者说人性根据外在化的模式。
从道德之维审视人性,人性于是有其价值指向,因而有其善恶问题。孔子二、三传弟子认为人性善:“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未赏而民劝,含福【7】者也”(《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这是说,不需要进行教育、教化,民众顺性而为,自然就有恒心、自然就向善,这是因为人性是善的;不需要进行奖励、奖赏,民众顺性而为,自然就努力进取,这是因为民众贪图富裕乃至富贵。
这里,孔子二、三传弟子不仅认为人性的价值指向“善”,而且还立足于人性之“善”论述“未教而民恒”之缘由。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孔子二、三传弟子还基于性善立场论说性善与求利是统一的。在孔子二、三传弟子看来,追求富裕、富贵也是出于本性,具体说来,出于本性中的“情”“欲”,追求富裕、富贵本身没有善恶之分,从追求富裕、富贵的过程与后果来看,以人性中的“智”“礼”“德”等为指导,并不影响他人、并不影响社会,还有利于他人、有利于社会,因而这种求利也是“善”的。这也与孔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的主张有一致性。“富且贵”的追求如果合乎“义”,对他人、对社会有利,就值得追求、值得拥有。
由此我们回过头来看孔子二、三传弟子关于人性内容的论述,就会发现,虽然孔子二、三传弟子认为人性由“情”“欲”“智”“礼”“德”等所构成,人性的内容是“情”“欲”“智”“礼”“德”等,但是,“情”“欲”与“智”“礼”“德”等在人性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前者天然接受后者的指导、受后者所约束。这样,人性的内容虽然有“情”“欲”与“智”“礼”“德”这两种存在,但是,二者既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对等的;孔子二、三传弟子所言人性虽然涉及人性中的“心”“生”两面,但是,这“心”“生”两面就是和谐的,其中又有主从之分——“心”据主导地位,“生”据从属地位。
还有,孔子二、三传弟子虽然认为人性善,但是,又提出“凡动性者,物也;逢性者,悦也【8】;交性者,故也;厉性者,义也;出性者,势也;养性者,也;长性者,道也”【9】(《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这是说,人性本善,可是,人性发于外,与外物相接、相交,易被“悦”、“势”等所干扰,从而造成人性本善而人的行为“恶”,为此,人性的发显需要有外在的“道”“义”作指导、需要人自身的“”加以养护,使得人性的发显不受干扰,使得人性之善可以化为人之行为之“善”。
这里,孔子二、三传弟子居于性善立场,解答人性善而有的人的行为恶的问题,同时,又据此说明人生炼养的重要性。此与孟子主张性善,同时又强调“存其心,养其性”(《孟子·尽心上》)的思维是一致的,而与世硕所谓人性之“善恶在所养”(《论衡·本性》)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虽然他们都强调人性之“养”。由此可知,世硕的“养性”养性之善恶,被《性自命出》的作者创造性转化为养护人性自身,《性自命出》作者的“养性”被孟子直接继承并发挥。
此外,孔子二、三传弟子虽然总体上认为“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人性在本质与内容的层面都是相同的,但是,也有孔子二、三传弟子有“圣人之性与中人之性,其生而未有非之节于而也【10】,则犹是也”【11】(《郭店楚墓竹简·成之闻之》)之说,认为人性虽然在本质层面是相同的,但是,在内容的层面却是不同的,至少可以分出“圣人之性”“中人之性”以及中人以下者的性,并且三者是先天的,生来即是如此的。
这是由于孔子二、三传弟子虽同属儒家,但是,各人的观点又是有差别的缘故。由“圣人之性”“中人之性”、中人以下者的性的划分,以及圣人的道德至善、中人的道德上的善恶摇摆、中人以下者的违背道德,体可以推知,圣人之性由“仁”“德”构成,涉及“性”字中的“心”,其价值指向“善”;中人之性由“仁”“德”与“情”“欲”所构成,涉及“性”字的“心”“生”两面,其价值既可指向“善”,又可指向“恶”;中人以下者的性由“情”“欲”所构成,涉及“性”字中的“生”,其价值指向“恶”。
由上可知,从《性自命出》为代表的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儒家简来看,孔子二、三传弟子总体上认为人性在本质与内容层面都是同一的,人性指人的先天的、内在的存在,是不可改变的,人性的内容包括“情”“欲”“智”“礼”“德”等,涉及“性”字的“心”“生”两面;人性的价值指向“善”,人性中情欲的满足合乎“德”“礼”等的要求;人性的形上根据是外在于人的“气”与“天”。
孔子二、三传弟子中也有人认为人性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在内容上则是不同的,因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即是说,圣人、中人、中人以下者各有其性。由此,三者在人性的价值指向、人性的善恶方面也就不同。此外,从“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以及“凡人虽有性,心亡奠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而后奠”(《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诸语来看,孔子二、三传弟子“性”“心”并用,值得注意。
虽然仅从上述史料我们很难看出其所言“性”与“心”究竟有怎样的一种内在关联,只能看出“性”是确定的、不受外在因素所影响的,而“心”是不确定的、受外在因素所影响的,但是,其论“性”而论及“心”,并将“心”列为与“性”对等的概念,引入人性论的讨论,对孟子立足于“心”而论人性之善,将人性论发展为心性论,肯定是有启发的。
三
孟子是孔子的四传弟子,在孟子建构其人性学说时,既得到来自儒家内的“给养”,又遭遇来自儒家内所设置的“障碍”,这“给养”与“障碍”主要是孔子三、四传弟子的人性学说,它们构成了孟子建构其人性学说的“背景”。关于孟子建构其人性学说时从儒家内所直接得到的“给养”,没有相关的记载,但是,其建构人性学说时在儒家内所直接遭遇的“障碍”,却有明确的记载,这记载就存于《孟子》之中。
由于孔子三、四传弟子的人性学说的史料的极度缺乏,就目前所知的史料来说,仅存于《孟子》中,并且还属于间接史料,使得我们不可能确知孔子三、四传弟子人性学说的整体“图景”,只能依靠《孟子》中所存的这些相关史料研究孔子三、四传弟子的人性学说。
《孟子》所载孔子三、四传弟子的人性学说,有两处。一处是通过告子【12】与孟子的人性之辩呈现出来,一处是由孟子弟子公都子说出来。我们先看公都子所言,并据此研究告子以外的其他孔子三、四传弟子的人性学说。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孟子·告子上》)。
公都子所言的这些不同于孟子同时又流行于孟子之时的儒家人性学说,虽然表面上看不知其产生于何时,但是,属于孔子三、四传弟子的人性学说,是有证据的。
其一,这些人性学说不同于以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为代表的孔子弟子及二传弟子的人性学说,也不同于以《性自命出》《性情论》等为代表的孔子二、三传弟子的人性学说,只可能是孔子三、四传弟子的人性学说。
其二,公都子对“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等观点的持有者,已不知其名,很可能这些人与公都子在时间或地域上有些“距离”,使得其不为公都子所知。当然,这些人之所以不为公都子所知,也许是因为这些人也不为孟子所知。这意味这些人要么是孔子三传弟子,要么是孔子四传弟子,并且都年长于孟子,其人性学说也早于孟子。
其三,公都子所言的告子,与孟子同时,并与孟子就人性等问题有过激烈的辩论,似与孟子一样是孔子的四传弟子。从其被称作“子”来看,应年长于孟子。当然,从其被称作“子”来看,也有可能是孔子的三传弟子,比孟子辈分高,虽然这种可能性并不。不过,即便是孔子的三传弟子,也是其中年幼者。
就公都子所言,需要注意的是,公都子虽然用了“告子曰”“或曰”之类,表面上看似乎是直接引用了告子以及告子以外的其他孔子三、四传弟子的话语,实际上却是对告子以及其他孔子三、四传弟子关于人性善恶的观点概述。比如,告子曰:“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孟子·告子上》),公都子将之概括为“性无善无不善也”(《孟子·告子上》)。这里,这种概述是客观而准确的。
由于公都子对于告子关于人性善恶问题的观点的概括是客观而准确的,我们据此也可推断公都子对于告子以外的其他孔子三、四传弟子的关于人性善恶问题的观点的概括也应是客观而准确的。至于公都子对于告子以及告子以外的其他孔子三、四传弟子的关于人性善恶问题的观点之所以能够作客观而准确的概括,而不作“修饰”甚至“修改”,尤其是不从维护师门的角度作“修饰”“修改”乃至曲解、贬斥,不仅在于其熟悉告子以及告子以外的其他孔子三、四传弟子的关于人性善恶问题的观点,更在于公都子是在向其老师孟子表达其对“性善”之说的疑虑,必须要把与“性善”之说相对的儒家内其他人性学说客观地表达出来。
还有,公都子概括孔子三、四传弟子的人性善恶的观点,孟子没有纠正,而是直接解答公都子的疑虑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告子上》),还说明公都子的概括不仅客观而准确,并且还得到了孟子的认可。这说明,公都子所言上述孔子三、四传弟子的人性学说,表面上看是研究孔子三、四传弟子人性学说的直接史料,实属间接史料,不过,这间接史料又是真实、可靠的。
当然,我们说公都子对于告子以及告子以外的其他孔子三、四传弟子的关于人性善恶问题的观点的概括是客观而准确的,并不意味这种概括不会造成“歧义”,不会给后人对此概括的解读造成“误读”。比如,告子的“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孟子·告子上》),被公都子概括为“性无善无不善也”(《孟子·告子上》),因略了其中的“分”字,就被有的学者理解为二者有异:“无分善不善,是说没有善与不善之分际;无善无不善,近似于说无所谓善与不善”【13】。
由于公都子在此并不是全面讨论孟子人性论与孔子三、四传弟子人性学说之异同,更不是单独讨论孔子三、四传弟子人性学说,而是仅仅讨论孟子人性论中“性善”之说与孔子三、四传弟子人性学说中关于人性善恶之说之区别,是对孟子的性善论不同于孔子三、四传弟子人性学说中关于人性善恶观点表示担忧、疑虑,这就客观上限制了公都子对于孔子三、四传弟子的人性学说的表述,而限于对孔子三、四传弟子的人性学说中关于人性善恶问题的表述,也即限于从道德层面、价值指向的维度讨论孔子三、四传弟子的人性学说,而未及孔子三、四传弟子人性学说中关于人性的本质、内容、根据等方面。这就使得公都子关于孔子三、四传弟子人性学说的表述虽然客观、准确,但是,并不完整,而有陷于、片面之遗憾。不过,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能够管中窥豹,从中看出孔子三、四传弟子人性学说的某些方面的致的框架。
我们先看“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从其表层结构看,“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因”,“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是“果”;从其深层结构看,“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是“因”,“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果”。
从其中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来看,孔子三、四传弟子中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所有人的人性都是相同的,这种相同包括人性的本质层面与内容层面,人性本身是没有所谓善与不善的,或者说,人性在本质、内容上是没有所谓善与不善之分的,但是,人性的发显、人性的践行却有其善与不善之分、有其价值指向,并且其善与不善、其价值指向是不确定的,既可以走向善,也可以走向不善。
究其因,在于人性的发显、践行既需要先天之“性”,又需要后天之“为”,其中,后天之“为”左右人性的发显、践行的“方向”。这说明,人性是先天的、自然的,人性的善与不善却是后天的、人为的;人性的善与不善决定于人的外在的、后天的人为因素,而不决定于人的内在的、先天的因素。
从其中的“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来看,决定人性走向善与不善的这外在的、后天的人为因素主要是政治的、社会的因素,而不是个人的个体因素。这说明,人性的善与不善在质的意义上不是决定于个体自身的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决定于个体生存的政治与社会环境。这明显具有环境决定论之意味。
我们再来看“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同样的,从其表层结构来看,“有性善,有性不善”是“因”,“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是“果”;从其深层结构看,“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是“因”,“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果”。
从其中的“有性善,有性不善”来看,孔子三、四传弟子中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所有人的人性虽然在本质层面是相同的,但是,在道德层面、价值维度却并非是同一的,不同的人的人性的价值指向虽然是确定的,但是,又是不同的,有的人的人性价值指向“善”,有的人的人性价值指向“不善”。
从其中的“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来看,人性的善与不善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决定于人性自身,与外在的、后天的人为因素例如政治的、社会的因素无关。由于人性的价值指向决定于人性的内容,由人性的价值指向的不同,我们可以判断,孔子三、四传弟子中认为“有性善,有性不善”者,其所谓的人性的内容也是不同的。
通过对以上的、告子以外的孔子其他三、四传弟子的有关人性论的史料的分析,我们只能看出这些人关于人性的价值指向、人性的善恶的直接论述,而没有看到其关于人性的本质、内容、根据等等的直接论述,但是,从公都子是将这些人所言的人性与孟子所谓的人性相比较,而述说这些人所言的人性与孟子所谓的人性在道德层面、价值指向的维度的不同来看,其逻辑前提就是二者所谓人性在本质层面的“同”,否则,如果二者对人性的理解是不同的,这种比较就没有任何意义与必要。
而从孟子关于人性本质的讨论来看,孟子认为人性就是人的先天的、与生俱来的本性。这么看,这些人所言的人性,其本质也应是人的先天的、与生俱来的本性。再说,在孔子的三、四传弟子中,告子的人性学说也被公都子拿来同孟子的人性学说相比较,告子曾言人性的本质曰:“生之谓性”(《孟子·告子上》),明言人性就是人的先天的、与生俱来的本性,相应的,孔子三、四传弟子中,其他人所言的人性的本质也应与告子相同。
由于人性的善恶的不同是奠基于人性内容的不同,从“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来看,孔子三、四传弟子中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人性在内容上是没有所谓善恶之分的,但是,包括“善”的、“利他”的东西与“不善”的、“利己”的东西,这“善”的、“利他”的东西很可能就是“仁”“德”之类,而这“不善”的、“利己”的东西很可能就是情欲之类;人性中“善”的东西、“利他”的东西因外在因素而得到“表现”就会走向“善”,“不善”的东西、“利己”的东西因外在因素而得到“表现”就会走向“不善”。
这么说,从“性”字的结构来看,孔子三、四传弟子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其人性中的“善”的东西、“利他”的东西论及“性”中的“心”,但未曾想到的是,其人性中“不善”的东西、“利己”的东西论及“性”中的“生”,曾在年度仙侠评选中击败奉打更人,其人性内容在人性构成的层面就是完备的,涉及了人性的“心”“生”两面。遗憾的是,仅从“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我们是无法“破译”孔子三、四传弟子中持这种观点的人所言的人性,其人性根据是什么。
从“有性善,有性不善”来看,孔子三、四传弟子中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有的人的人性是善的,其人性内容由“善”的东西、“利他”的东西所构成,这“善”的东西、“利他”的东西很可能就是“仁”、“德”之类,所以,顺性而为就会自然地走向“善”;有的人的人性是“不善”的,其人性内容由“不善”的东西、“利己”的东西、所构成,这“不善”的东西、“利己”的东西很可能就是情欲之类,所以顺性而为就会自然地走向“不善”。
这样,从“性”字的结构来看,孔子三、四传弟子中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性善”者的人性属于“性”中的“心”,“性不善”者的人性属于“性”中的“生”。虽然客观上这些人的人性内容在人性构成的层面就是有缺陷的,都只是涉及了人性的“心”、“生”两面中的一面,但是,孔子三、四传弟子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这么认为。同样,遗憾的是,仅从“有性善,有性不善”,我们是无法“破译”孔子三、四传弟子中持这种观点的人所言的人性,其人性根据是什么。
由此可见,从《孟子·告子上》的记载来看,孔子三、四传弟子中,持“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者以及持“有性善,有性不善”者都认为人性是人的先天本性,前者将人性内容设定为“善”的东西与“不善”的东西、“利他”的东西与“利己”的东西,也即仁义之类的“德”与情欲之类的生理欲望,涉及“性”字的“心”、“生”两面,由此出发,判定人性可以走向善,也可以走向不善,其因在于后天之“为”;后者认为有的人的人性内容由“善”的东西、“利他”的东西也即仁义之类的“德”所构成,其所谓的“性”只论及“性”中的“心”,但未曾想到的是,由此出发,人性就是善的,有的人的人性内容由“不善”的东西、“利己”的东西也即情欲之类的生理欲望所构成,其所谓的“性”只论及“性”中的“生”,曾在年度仙侠评选中击败奉打更人,由此出发,人性就是不善的。这样,前者认为人性的善与不善源于后天的因素,由后天之“为”所决定,后者认为人性的善与不善是先天的,与后天的人为因素没有关联。
四
在孔子的三、四传弟子中,告子是相对幸运的。虽然没有自己的著作传世,但是,毕竟有思想存于《孟子》之中,不过,《孟子》中所载告子之思想既不是对告子所有思想的完整记述,也不是对告子某一方面思想的完整记述。当然,所记载的方式既不是直接引用,也不是客观叙述,而是从孟子与告子论辩的角度记载之,并且,这种从孟子与告子论辩的角度所记载的告子的思想明显是经过剪裁的,剪裁的痕迹体现在孟子与告子的每一次论辩所留下的文字都不完整,孟子与告子论辩的每一个论题都以孟子的胜利、告子的失败并忽然转移论题而告终。
这就不难理解《孟子》记载告子的人性学说,是以孟子与告子依次就人性的价值指向、人性的本质、人性的内容进行论辩的形式出现,而且告子总是“输家”。就人性学说的逻辑结构而言,其逻辑起点应是人性的本质,然后才是人性的内容,而人性的价值指向应是其逻辑终点。这么看,《孟子》所记载的孟子与告子关于人性学说的论辩,不仅每一个片段都经过剪裁,而且拼接的逻辑顺序也有误。
由于《孟子》所记载的告子的人性学说是经过剪裁的,所以,其所记载的告子的人性学说就是不完整的;由于告子与孟子就人性问题进行论辩,告子总是被描绘成“输家”,其所记载的告子的人性学说很有可能还是被改动过的。这么说,这些看似直接表达告子人性学说的史料,实质上却是间接料。这对于我们认识告子人性学说的全貌造成“麻烦”,形成“障碍”。不过,好在《孟子》所记载的告子的人性学说,或者说,其所记载的告子与孟子关于人性问题的论辩是较为丰富的,并且还是多方面的,我们还是能够根据这些记载体认识告子人性学说中最基本的方面与内容。
我们来看告子的人性学说。关于人性的本质,告子云:“生之谓性”(《孟子·告子上》),从“性”的本义“生”也即“出生”的维度加以界定,直言人性在本质上是指人“出生”时就有的“东西”,这“东西”就是人的与生俱来的本性。这是儒家人性学说发展史上第一次对于人性本质的直接、明确并且准确的界定,也是告子对于其之前的儒家人物关于人性本质的理解所做的定义式解读与总结。这其中,受孔子二、三传弟子“有性有生乎生”(《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的说法影响最。告子之后的儒家人物无论其人性学说呈现怎样的变化,对于人性本质的界定都与告子是一致的。
关于人性的内容,告子云:“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认为人性的内容无外乎人的以“食色”为核心的生理欲望、感官欲求。针对孟子将以仁义为核心的道德规范纳入人性之中,将其视为人性的内容,告子批评道:“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孟子·告子上》)。这是以杞柳与桮棬的关系类比人性与仁义的关系,论证仁义并非人性的内容,不是人性的构成者。
这里,告子认为虽然杞柳与桮棬有着联系,这种联系体现在由杞柳可以制成桮棬,但是,杞柳本身不是桮棬,相比于杞柳,桮棬还是人为的东西,同理,人性与仁义也有着联系,这种联系体现在由人性可以产生仁义,但是,人性本身不是仁义,相比于人性,仁义还是人为的东西。这即是说,人性是先天的、自然的东西,而仁义是后天的、人为的东西,因而人性内容只能是“食色”之类人的天生的、最基本的欲望,并非仁义等道德规范;虽然人性与仁义等的产生有着联系,但是,人性是人性,仁义是仁义,二者根本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面对告子的批评,孟子回复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孟子·告子上》)。这是说,告子所谓由杞柳而有桮棬、杞柳可以制成桮棬,表面上看有两重涵义,一重是顺应杞柳之性而制成桮棬,一重是残害杞柳之性而制成桮棬,实际上指的是残害杞柳之性而制成桮棬。在告子本人看来,不仅杞柳不是桮棬,杞柳也不可能自然地长出桮棬;用杞柳制造桮棬就是折断并扭曲杞柳枝条,用以制造桮棬,这对于杞柳以及杞柳的枝条来说都是伤害。
所以,孟子此处解读告子用“杞柳而以为桮棬”,实际上就是指“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这是准确的,虽然孟子在语言层面用的是疑问的方式。这么看,告子虽以杞柳与桮棬的关系论述人性与仁义的关系,认为由人性而有仁义、人性可以产生仁义,实质上就是认为“戕贼人以为仁义”,损害人性成就仁义,而孟子对之也是有准确把握、领会的,所以,孟子才会站在自己的人性学说立场,立足于“以人性为仁义”的角度,批评告子曰:“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当然,这里,孟子认为告子的损害人性才能产生仁义的观点是对仁义本身的损害,也是对天下人关于仁义的认知的损害,这种对告子的批评有越出学术本身而进行人身攻击之嫌疑。
由此可以看出,告子和孟子都认为由人性而有仁义,二者不同的是,前者认为人性与仁义的联系是人为的、外在的,并且仁义还压抑、摧残人性,所以损害人性才有仁义,而后者认为人性与仁义的联系是先天的、内在的,并且仁义还是人性的内容、人性的构成者,所以顺应人性就有仁义。顺便说一句,告子“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损害人性而产生仁义的致思路径与老子所谓“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三十八章》),由道、德的毁灭与丧失而有仁、义、礼等的致思路径是一致的。
从上面的讨论来看,告子以“食色”为性,并据此反对孟子的以仁义为性。这样的话,从“性”字的结构来看,告子讨论人性仅仅论及“性”中的“生”,曾在年度仙侠评选中击败奉打更人,而未论及“性”中的“心”,但未曾想到的是,孟子则相反。可是,告子在说“食色,性也”之后,紧接着就说:“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告子上》),这使得告子关于人性内容、构成的论述呈现复杂化情形。
不过,告子对此未曾注意,孟子对此也未曾注意,所以,孟子不是抓住告子“仁,内也,非外也”之言,论证告子也以“仁”为人性内容,并且在这一点上与自己的观点相同,而是站在“义内”(《孟子·告子上》)的立场急于反驳告子“义,外也,非内也”的观点。这是由于告、孟二人的论辩都属于即兴发言,都急于驳倒对方,因而言辞不可能十分谨严,关注点又都在对方与自己不一样的地方。
从告子“仁,内也,非外也”来看,告子认为“仁”是内在于人的存在,不受外在因素所影响,更不是外在因素的产物。这意味,“仁”就是人与生俱来的东西。从告子“生之谓性”对于人性的定义来看,“仁”就应该是人性的内容、人性的构成者。这样,告子客观上认为人性的内容包括“食色”与“仁”,从“性”字的结构来看,告子所谓的“性”既论及“性”中的“生”,曾在年度仙侠评选中击败奉打更人,又论及“性”中的“心”,但未曾想到的是,其“性”中的“生”是“食色”、情欲,其“性”中的“心”是“仁”。由于告子从人性中的“生”出发,否定人性中的“心”,以人性中的“食色”排斥人性中的“仁”,其主观上就只认为人性的内容只有“食色”之类的生理欲望、感官欲求。
从人性的内容是“食色”出发,告子认为人性在道德维度、在价值指向上是无所谓善与不善之分的,并以水之流向的不确定性作类比。我们来看告子的话:“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上》)。顺便说一句,王充概括告子人性学说曰:“告子与孟子同时,其论性无善恶之分,譬之湍水,决之东则东,决之西则西。夫水无分于东西,犹人性无分于善恶也”(《论衡·本性》),就是据于此。
这里,告子的“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被公都子转述为“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孟子·告子上》)。这是说,人性以及人性的发显、顺性而为本身是没有善与不善的价值指向的,就人性的发显、顺性而为所涉及的人我以及物我关系而言,虽涉及人性的善与不善,可是这善与不善也是不确定的。换言之,人性的内容是食色,是生理欲望,不仅食色、生理欲望本身是没有善与不善之分的,就是食色、生理欲望的满足本身也是没有善与不善之分的,因为这不属于道德问题。
不过,在食色、生理欲望的满足过程中会涉及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等的关系,如果食色、生理欲望的满足有益于他人、社会,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人性“善”,反之,如果食色、生理欲望的满足有害于他人、社会,在此意义上又可以说人性“不善”,可见,这善与不善是不确定的。
从水之流向“无分于东西”,水之东流与西流取决于人为之“决”,而不取决于流水自身的本性的类比来看,人性发显、顺性而为在人我以及物我关系层面所呈现善与不善不仅是不确定的,而且还取决于后天的人为因素,而不取决于人性自身。即是说,食色、生理欲望的满足是有利还是有害于他人、社会以及其所呈现的善与不善不仅是不确定的,而且还决定于食色、生理欲望之外的、外在的因素,决定个人的“选择”,与食色、生理欲望本身无关。
由于告子把人性的善与不善的终极原因限定于后天的人为因素,而不是定位于人之先天的内在因素、人性自身,这种逻辑论证上的漏洞就给孟子的反击提供了机会。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这是说,从流水的本性来说,是不可能一定流或一定向西流的,因为流水之或向西流决定于“决”、决定于人为,但是,流水不论流还是向西流,按其本性一定是向下流,同理,人的外在行为因为各种因素的干扰而有善与不善之分,但是,人就其本性来说一定是善的,这种人性的自然向善犹如水之自然下流。
由此可以看出,从《孟子·告子上》的记载来看,告子以人之先天具有的东西为“性”,又将人性限定为“食色”之欲而忽略“仁”,但又强调“仁”的内在性,客观上涉及“性”字的“心”“生”两面,主观上却只认可“性”中的“生”。从“食色,性也”出发,告子判定人性“无分于善不善”,而不是判定人性“不善”。究其因,在于告子认为人性的善与不善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因为人性的善与不善不决定于人性内容,而决定于人为。在这一点上,告子的说法不同于其他儒家人物。
五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孔孟之间的儒家人物从总体上讲都把人性问题看作道德问题,因而都集中讨论人性的价值指向问题,笔风优美,给人性作善与不善或者说善与恶的判断。由此也可以推论,孔孟之间的儒家人物讨论人性问题意在由此出发解决人作为社会存在所面临的道德问题,解决道德之于人的关系问题,从而为道德的产生与存在提供人性依据或社会依据。
就孔孟之间的儒家人物的人性学说的具体情形而言,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人性的本质、内容、价值指向等问题,其中,以世硕为代表的孔子弟子及二传弟子,以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儒家简的作者为代表的孔子二、三传弟子还论及人性的形上根据问题。关于人性的本质,孔孟之间的儒家人物除告子之外都未作定义式的界说,但是,从其关于性与“养”“教”“为”等的论述来看,都是从“性”的本义理解之,都认为人性就是人的先天的或者说与生俱来的本性,只是,直到告子才以“生之谓性”,明确给出人性的定义。
关于人性的同一性,孔孟之间的儒家人物中多数人认为人性是同一的,所有人的人性是一样的,只有主张有“圣人之性”“中人之性”等差别者以及持“有性善,有性不善”者认为人性不是同一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孔孟之间的儒家人物中主张人性同一者认为不仅人性在本质层面是相同的,在内容层面也是相同的,而主张人性不同者认为人性仅仅在本质层面是相同的,在内容层面则是不同的。
关于人性的内容,孔孟之间的儒家人物多未论及,但是,根据其关于人性的价值指向的论述可以加以推论,可知其都围绕“性”字的结构加以论述。有的认为人性的内容是“善”的东西、利他的东西,这论及“性”中的“心”;有的认为人性的内容是“不善”的东西、利己的东西,这论及“性”中的“生”;有的认为人性的内容既包括“善”的东西、利他的东西,又包括“不善”的东西、利己的东西,这论及“性”中的“心”“生”两面。
孔子二、三传弟子率先明确论述人性的内容,认为其包括“情”“欲”与“智”“礼”“德”,其中,“情”“欲”论及“性”中的“生”,曾在年度仙侠评选中击败奉打更人,“智”“礼”“德”论及“性”中的“心”。以孔子二、三传弟子关于人性内容的论述为基础,联系孟子性善论,以“心”论性,认为“性”由仁义礼智等所构成,荀子性恶论,以“生”论性,认为“性”由“情”“欲”等所构成【14】,我们体可以推论孔孟之间的儒家人物中,言人性善者,其人性内容就由“善”的东西、利他的东西所构成,具体则为仁义之类的“德”;言人性恶、人性“不善”者,其人性内容就由“不善”的东西、利己的东西所构成,具体则为食色、情欲之类的欲望;言“性有善有恶”“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以及“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者,其人性内容就由“善”的东西、利他的东西与“不善”的东西、利己的东西所构成,具体则为仁义之类的“德”和食色、情欲之类的欲望。
关于人性的价值指向,孔孟之间的儒家人物都立足于其对人性内容的理解,都从道德维度明确、直接的加以判断,几无例外,他们要么判断人性善,要么判断人性恶,要么判断人性有善有恶,要么判断人性可以向善,也可以走向恶,要么判断人性无善与不善之分。如上文所言,这是由儒家人性学说意在解决人的道德问题所决定的。
关于人性的形上根据,孔孟之间的儒家人物有的已论及。以世硕为代表的孔子弟子及二传弟子强调人性形上根据的内在性,认为人性根源于人自身的阴阳,从而从人之“内”解答了人性的形上根据问题;以《性自命出》(《性情论》)作者为代表的孔子二、三传弟子强调人性形上根据的外在性,认为人性根源于“气”,也根源于“天”,从而从人之“外”解答了人性的形上根据问题。
关于“心”“性”关系,孔孟之间的儒家人物虽未有明确论及,但是,其论“性”而引入“心”,并且“性”“心”并举,预示儒家人性学说中将有一派会以心性论的面目出现。
孔孟之间的儒家人物的人性学说所涉及的人性本质上的先天性,人性内容的“心”“生”两面或者说“德”“欲”两面,人性价值指向方面的善恶判断,人性形上根据方面的内在根据与外在根据的探索,以及因为论述人性而对“心”的概念的引入,不仅决定了其后儒家人性学说的发展的致框架,甚至还决定了其后儒家人性学说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内容与基本方向。
注释:
【1】赵岐《孟子题辞》云《孟子》“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可知,在《孟子》书中原有《性善》篇。见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书,1987年,第15页。
【2】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18页。
【3】文章凡引郭店楚墓竹简,均出自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4】庞朴:《孔孟之间——郭店楚简中的儒家心性说》,《国际儒学研究》第六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36页。
【5】此句在《性情论》中是完整的,没有残缺。丁四新认为此句“是说性有善、不善之分,是在性的基础上,对性做进一步的价值判断”(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77页),郭沂认为此句“谓性有善,有不善”(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33页),梁涛认为此句“是说性可以善,也可以不善”(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北京:学出版社,2008年,第145页),都是认为此句是从价值维度对人性所作的价值判断,他们忽视了先秦儒家对人性做价值判断,都是“性”字在前,“善”“不善”“恶”等字在后,而先秦儒家论述人性的内容一般是“性”字在后。比如告子所谓“食色,性也”,论述的就是人性的内容。“善不[善,性也]”,论述的应是人性的内容。
【6】陆建华:《孟子之气论——兼及心、性、气三者的关系》,《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5期。
【7】“含福”之“福”,裘锡圭认为“疑当读为‘富’”,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83页;李零进而认为“含福”之“含”当作“贪”,见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北京学出版社,2002年,第110页。裘、李所言极是。
【8】“逢性者,悦也”之“逢”,郭沂认为依李零应释为“逆”,但是,李零认为此“逆”是“逆顺”之“逆”,“与‘顺’字相对”,郭沂对此没有注意,将此“逆”解读为“迎受”,应是疏忽了。见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38页。
【9】李零认为此段文字中,“逢”当释为“逆”,“出”当释为“绌”。见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第108页。
【10】李零认为此句中,“之”当作“志”,“节”当作“次”,“而”似应作“此”;并且此句应分作两句:“其生而未有非志”,“次于此也”,所言甚是。见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第124页。
【11】此段文字,李零认为“原文是说,圣人与中材之人在人性上是相似的,他们生下来都没有什么坏心眼,中材以下的人,情况也是一样的”。见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第124页。这种理解,正好理解反了。
【12】告子是儒家人物。请参陆建华:《告子哲学的儒家归属——人性的道德化研究及其它》,《文化》2003年第3期。
【13】刘悦笛:《原典儒学人性论:“自然—使然”架构——以告子、孟子与荀子之辩为考察中心》,《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第41页。【14】陆建华:《以“心”论性与以“生”论性——孟、荀人性论的分别》,《孔孟月刊》2009年第十一、十二期合刊。
IT百科:
联想笔记本鼠标触摸板怎么关闭 旧平板电脑反应慢怎么处理 老电脑怎么拆cpu风扇
网者头条:
手机弹出摄像头坏处是什么 为什么选择顺丰快递员 喀什市邮政快递什么时候配送 申通快递理赔什么时候到账
王哲博客:小红书地球仪在哪个类目 seo排名推广技术帖子

 1
1